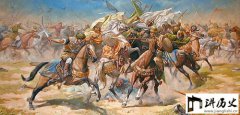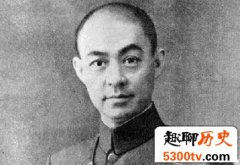郅支之战:中国军队历史上到达的最西端的战争之一 汉朝以夷制夷的典范
【千问解读】
郅支之战是公元前36年发生于西汉与匈奴首领郅支单于之间的一次战役,郅支单于战败被杀。
这场战役发生于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塔拉斯河畔的塔拉兹附近,这里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到达的最西端之一。

焦点的西移
经过连年征伐,汉朝的老对手匈奴,开始态势衰颓。
随着贵族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单于继承制度越来越混乱。
汉朝的国力优势压制与周边各部族的起而反抗,都让匈奴的草原霸主形象,岌岌可危。
在西域北部,斯基泰血统较重的乌孙,获得了汉朝的大力扶持。
南方的西域六个城邦联军也趁火打劫,攻破了匈奴的铁杆盟友车师国。
最后,匈奴负责西域事物的贵族日逐王投降汉朝。
但残存的匈奴势力,依然在北面的乌孙与汉朝继续争夺。
此外,一些人开始利用中亚的乱局,进入了位于索格狄亚那的大联盟--康居。
公元前64年,匈奴人首先尝试将汉朝势力逐出乌孙。
他们趁着亲汉朝的旧王去世,拥立两代匈奴与斯基泰混血的贵族为王。
汉朝只能再次实战军事压力,将整个乌孙人分为两群。
此后,汉乌混血的王子立为大王,将乌匈混血的王子立为小王。
他们的都在名义上成为了汉朝的附属国,但汉朝公主刺杀乌孙王的行为却引发了乌孙人的争议。
结果便是亲匈奴的乌孙势力,再次获得优势。
在蒙古高原,两位单于韩邪和郅支,却在为争夺大汗之位而内斗不休。
呼韩邪单于选择归顺汉朝,并在汉人保护下羽翼丰满,回到了单于庭故地。
处于不利地位的郅支,开始向汉朝不断示好。
他的努力让汉朝一度产生所觉,认为自己成功的用南匈奴制约了北匈奴势力。
结果,郅支趁着呼韩邪去长安朝拜会皇帝的机会,夺取了靠西的匈奴右地,杀死了另一个自立为单于的贵族。
随后,他的军队连续击败了乌孙、乌揭、丁零等民族,国力复振。
有了底气的郅支,还以内附为诱饵,要回了自己在长安当人质的王子。
等到儿子回国,他就翻脸杀死了汉朝使节。
正在此时,位于今天河中的康居人,在与乌孙人的战争中失利。
软弱的国王开始傲请北匈奴来支援自己作战。
得到邀请后的郅支单于,率领50000人马向西进军。
在遭到严重的雪灾袭击后,最终和剩余的3000残余,来到了康居。
他们在当地,联合了等待多时的索格狄亚那斯基泰人,多次击败了亲汉朝的乌孙部落。

汉朝的西域新模式
汉朝在西域与中亚东部的声望,在第二次远征大宛后,也有了很大提升。
吸取了过往经验教训的汉朝,开始用一套更为多元而有效的模式,对西域各地进行分而治之。
汉朝初期,出使西域的使节主要由书生士大夫或氓流冒险家担任。
前者的之乎者也,在语言文化隔阂甚重的西域,难以获得当地人的理解尊重。
后者则根本是利用身份,两头欺骗,为自己谋求一次性经济利益。
这都给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正常外交活动,蒙上了阴影。
动不动就征用全国民力进行的远征,也绝非长远之计。
因而,在与大宛的战争结束后,汉朝开始派遣有经验的军人,出任使节和官员。
由于有军事素养,他们在执行外交任务时,可以辅以军事手段来达成目的。
同时,汉朝更多的发动西域当地的盟友部队,为自己作战。
在这种新思路下,汉军联合乌孙人去惩戒勾结匈奴的龟兹国。
发动联军,攻灭了车师国。
一系列新的军事屯田区,也在西域各地建立起来。
当地的小规模驻军,可以通过屯田方式,减轻对内地物资供给的依赖。
当周遭小国发生突变,他们也可以迅速开展斩首行动。
用于贿赂西域贵族的赏赐物资,也通过这些控制区来安全抵达当地。
如果未来有大战爆发,那么这里也是安全的行军线路和补给基地。
很快,中亚局势的变化,就让汉朝人的西域新模式得以发挥奇效。
在索格狄亚那的郅支单于,以康居王不尊重自己为借口,杀死了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属下。
当地松散的城市与部落政治,让很多地方贵族对软弱的国王,往往难以服从。
郅支也就很快成为了一些地方派拥护的新盟主。
他动用当地人力,在锡尔河边建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郅支城。
在这个新首都内,他不仅扶持了一个康居贵族做副王,还要求费尔干纳的大宛与远在高加索东部的阿兰人向自己纳贡。
照此情形发展下去,这批西逃的匈奴人,很可能在河中聚集起一大帮敌视汉朝的政治联盟。
面对几位赶来的汉朝使节,他都毫不留情的将他们处死。
这种肆无忌惮的快速发展,也让汉朝掌管西域的陈汤和甘延寿决定对其用兵。

反郅支联军
由于西域将在未来的匈奴反击中,首当其冲。
当地军政长官们,都觉得有必要对索格狄亚那地区发起远征。
但他们还需要先向远在长安的朝廷进行请示,否则就无法调动各屯田区的全部力量。
军事素养较高的陈汤,却不希望让中间环节浪费了兵贵神速的良机。
当坚持先向朝廷禀报的甘延寿表示犹豫后,他就擅自伪造了朝廷诏令,让西域各地的汉军与同盟军进行集结。
甘延寿在最后时刻才发现这一情况,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阻止,便加入了这支混合大军。
公元前36年,一直约40000人的联合部队被组建起来。
汉朝安排在西域各地驻守的力量,自然是这支军队的核心。
但他们的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西域当地农耕条件最优越的轮台和渠犁地区,在巅峰时期不过有3000汉军驻扎。
大部分时候,他们的人数仅有1500人左右。
扼守塔里木盆地的楼兰,最初只有40人驻扎,此时才逐渐增加到1000人左右。
至于位置险要的车师,驻军数目不过在300人以上。
算上在乌孙境内驻扎的3000多人,汉军的直属兵力是并不足以发动大规模攻击。
在剖去了留守人员后,正在参加远征的人总计不超过3000多人。
真正承担远征部队主力的,还是陈汤假借朝廷号令,动员起来的西域同盟部队。
在这些盟军中,最为卖力的无疑是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带来的匈奴骑兵。
和他们一样有着较强作战欲望的是被郅支屡次攻击的乌孙亲汉朝部落。
至于塔里木盆地一带的大小国家,各自可有200—20000多人不等的战兵。
正是他们的部队,组成了40000大军的绝大部分。

分进合击策略
虽然陈汤成功的拉起了40000人的联军,但他知道自己的这点优势,很容易被各种内因与外因所共同稀释。
由于索格狄亚那地区距离西域有一定距离,其进军的艰难程度将超过当年李广利对大宛的远征。
郅支单于西征时,带去的大部分部队就在半途中被恶劣气候所消灭。
汉军的主力与西域联军中,又不乏很多缺乏乘马的步兵,进军速度会更加漫长。
此外,虽然陈汤不会知道中亚历史上的一些大规模征服战事,但索格狄亚那地区的斯基泰部落们,的确曾让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都耗费多年精力。
形散神聚的部落集团,不仅易于坚持抵抗的领袖游走,也能让抵抗者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兵力反击。
汉军过去在蒙古高原与费尔干纳地区,都遭遇过类似情况。
经常担任边防职务的陈汤,自然对此有一定认识。
最后,担任联军主力的西域部队,大都战斗力不高。
陈汤本人就认为,由于装备与战术问题,西域小国军队的战斗力比汉军往往是在5:1。
双方在有了一段接触后,西域各国学习了汉军的战术,才把差距缩小到3:1。
在汉军深入西域之前,当地军队实际上很少有对匈奴人的胜迹。
于是,陈汤的大军效仿当年李广利的第二次远征,分别走了南北两路。
所有西域小国的军队,一律走南路。
他们将沿着李广利军的祖籍,越过葱岭的支系山脉,首先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
这样一来,既可以让他们远离主战场,也能震慑可能帮助郅支作战的大宛人。
如果规模不大的匈奴人选择逃跑,那么他们的南路也已经被堵死了。
而费尔干纳地区较好的自然条件,也让行军速度较慢的大军有所保障。
至于战斗力较强的汉军步兵与匈奴、乌孙的骑兵,则走北路。
这段行军的环境与南路完全相反。
前期可以走汉军屯田区与乌孙人的草场。
等到进入康居边境,体力与状态保存较好的骑兵,可以立即展开行动。
天山山脉和伊犁河流域气候湿润,也让他们很容易搜集到制造攻城武器所需的木材。
得到汉军西征消息后,亲匈奴的康居副王抱阗,马上率领几千骑兵发起预防性进攻。
他们进犯乌孙人的赤谷城,杀伤1000多人,并劫掠了大量可能被用于补给的牲畜和牧民。
这些斯基泰骑兵,甚至出现在了汉军队伍的侧后方,突袭并抢夺走了汉军相当多的辎重。
陈汤于是下令匈奴与乌孙的骑兵,展开反击。
抱阗的骑兵因为携带劫掠来的畜牧与辎重,被联军骑兵轻易追上。
在一场典型的草原斯基泰式骑兵交战后,460名康居骑兵死在当场。
联军骑兵还抓住了一名带头的康居贵族,解救了470名被掳走的乌孙人。
汉军在释放乌孙俘虏的同时,顺便将那些牲畜都留作军用。
一路上,陈汤还严禁手下的各族士兵抢劫,给乌孙人与康居人以军纪严明的印象。
当北路军抵达索格狄亚那境内后,陈汤还亲自与很多当地的部落领袖会面。
他以斯基泰传统,与这些贵族们饮酒结盟。
很多原本就反对郅支的斯基泰酋长们,立即倒向了汉朝一边。
其他摇摆不定的中间派,则顺其自然的为汉军让道。
可以说,在最终交战之前,陈汤已经尽可能的在康居内部,孤立了郅支势力。

决战郅支城
陈汤在进军时间上,也非常巧妙的选择了秋冬季节。
在这个时节中,游牧民们往往要将人口与畜群集中管理,抵抗冬季的严寒。
大量部落在这段时间里,蜗居自己的城市和草场,彼此较为孤立。
郅支单于还是派出了使者,到周边的部落和国家寻求援助。
但陈汤的统战行军,已经让很多对单于不满的部落与匈奴人对立。
那些依然支持郅支的部落,则需要先自我评估一番参战后果。
然后,再从冬歇期中开展较慢速度的战争动员。
至于南面的大宛,在数万西域军队过境后,更不愿意冒险帮助匈奴人了。
汉军也为了不让郅支一伙人逃走,选择故意示弱。
他们在郅支城外30里地扎营,并向赶来试探的匈奴使者表示,自己的军粮快吃完了,能否活着回去都没把握了。
次日,他们又仅仅派出一小队人马,在城外3里处布阵。
以为汉军早已人困马乏的郅支,立刻决定应战。
100名匈奴骑兵主动出城列队,他们的两翼还有披甲持弓的斯基泰步兵掩护。
其余为数不多的匈奴人与斯基泰人,则在城头弯弓搭箭。
面对威胁的汉军,一直避免与郅支的部队发生近距离交战。
占据步兵绝大部分的弓弩手们,用密集的远射火力,射暴了企图抵近射击的匈奴轻骑兵。
数量有限的重骑兵,也在汉军的密集攻击下,被前排的盾兵所阻挡。
发现这样只是徒增伤亡后,他们转身向城门方向撤退。
随着更多汉军部队与同盟骑兵的突然赶到,匈奴骑兵在惊慌失措中,涌入城门。
追击的南匈奴与乌孙人,却不敢靠近有防御火力的城墙。
城门两侧的斯基泰步兵,则在标志性的大盾牌掩护下,用复合弓火力射退了他们。
这些典型的草原式步兵,因为第一排武士习惯放置于身前的一人高大盾牌,而被汉朝目击者称为鱼鳞阵。
但他们主要是依靠弓箭为杀伤手段。
当确定匈奴残兵完成撤退后,他们也就顶着汉军的新一轮射击,以完整的阵列入城。

此后,汉朝大军将郅支城围的水泄不通。
大量同盟军以辎重车在远处围成圆形的设防阵地,派出骑兵巡游周遭地带。
汉军则依靠大盾牌掩护,用弓弩与城头的守军对射。
郅支城是典型的斯基泰式堡垒,在木质的外墙被汉军焚火烧毁后,守军继续退到夯土构造的卫城土台顽抗。
深受草原武士文化浸染的郅支单于,还发动了自己的几十位后宫娘娘等楼作战。
这些草原女豪杰在汉军的密集火力下,也是折损过半。
单于本人的鼻子,也被箭矢射伤。
最后时刻,约10000人的亲匈奴康居骑兵,姗姗来迟。
他们分成十几队人马,绕着围城军队的阵地奔走,企图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但除了收获围攻者的箭矢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成果了。
一晚上的折腾后,他们在白天开始先行撤退。
已经杀入城中的汉军,则继续用火攻的方法,围逼堡垒内的残余守军。
当冲车终于撞破厚实的土墙,堡垒内的1500多匈奴与康居人被杀,郅支单于本人也被砍了脑袋。
郅支城之战,无疑是一场在开始前就已分出胜负的战役。
陈汤在康居等地,以夷制夷的杰出外交手段,让匈奴单于在开战前就被严重孤立。
选择在冬季作战,不仅让城里的敌人来不及疏散,也严重影响了他们向同盟部落的求援行动。
虽然汉军无法保持在葱岭以西的长期存在,但这样的胜利无疑瓦解了匈奴势力在中亚重振旗鼓的可能。
陈汤在一系列战略战术的选择上,无疑比强行实施虽远必诛的那些前辈们,高超了不少。
夷陵之战刘备损失5万人 蜀汉为什么就一蹶不振了
夷陵之战只是战败,为什么刘备突然就病死了呢?
荆州的失守,对刘备是一个沉重打击,不仅使原来准备分兵两路北取中原的计划破产,而且失掉了一个重要战略地区。
刘备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意夺回荆州,称帝后不久(同年七月),便亲率 五六万大军,东征。
01、东征孙权 对于刘备的东征,在蜀汉内部,有些人是持异议的。
如赵云就曾对刘备说: 国贼是,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灭掉曹魏,孙吴自然就会降服。
现在曹操虽死,但篡汉,应当利用人们对篡汉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凶逆。
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一定会带着粮食赶着马车来迎接王师。
因此,不应把曹魏搁在一边,先和孙吴争战。
战争一起来,一时解决不了,将造成不良的后果。
” 赵云这一先进兵讨伐头号敌人曹魏的意见,是可取的。
但刘备听不进去,他夺回荆州的决心下定了。
这时的孙权,对曹魏则抱着靠近的态度。
曹丕称帝后,孙权立即派人祝贺,并将投降后落在自己手中的魏将送回许都。
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孙权称臣于魏,是为了争取时间,稳定新占荆州的统治,免得曹魏进攻自己;当蜀汉进攻时,希望曹魏能保持中立,防止两面受敌。
因此,当曹魏使臣携带吴王的印绶来到东吴时,孙权表示非常欢迎。
他对部下说:“以前也接受过的分封,当汉王,这是权宜之计。
现在曹丕封我为吴王,又有什么不好呢?”于是接受吴王的封号,定年号为黄武。
对于蜀汉的进攻,孙权是做了一些准备的。
他把都城从建业迁到长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便于扼守荆州;又任为镇西将军,统领李异、刘阿等进驻巫县(今重庆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加强西线防务。
他还派使臣到蜀汉,要求重归旧好,刘备不同意。
刘备率军东下后,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孙桓等大将及战士五万人,西上拒敌。
02、张飞之死 刘备率军出发时,派人送信,调驻守在阆中(今四川阆中) 的车骑将军张飞,领兵万人到江州(今重庆)会合。
张飞虽然作战勇猛,有万人敌之称,但性急如火,而且对部下态度粗暴, 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引起部下对他的不满。
刘备曾劝诫张飞说:“你刑杀过分,又经常鞭打健儿,还让他们不离左右,这是取祸之道。
”刘备要张飞改变对部下的态度和提防左右生变,张飞不听。
这次张飞领兵出发时,帐下将领张达、范强伺机将他杀害,带着他的首级,投奔孙权去了。
张飞被杀的消息传来,刘备更加震怒,继续领兵东进。
当刘备到达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时,孙权又派遣使者前来求和,诸葛亮的哥哥(字子瑜),当时任孙吴南郡太守,也写信给刘备,劝他解仇继好,停止用兵。
刘备不听。
蜀汉军队的先头部队,在将军吴班、冯习率领下,首先打败吴军李异、刘阿部于巫县,然后进兵秭归。
当刘备从秭归领兵出发时,治中从事黄权谏阻说:“吴人悍战,而且我们水军顺流东下,进易退难,我请求当先锋同敌人较量,试探其虚实,陛下应该为后镇。
” 刘备不听,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长江北岸诸军,防备魏军进击蜀军侧翼,自己亲率大军在南岸沿山势东进。
刘备还派到沅水流域 ”地区,争取他们出兵配合。
武陵郡的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率众北上,协助刘备作战。
03、猇亭对峙 222年二月,蜀军进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长江北岸)设立了大本营。
前部则到达夷道(今湖北宜都),将孙权侄儿孙桓率领的一部分吴军包围了。
当时,吴军的一些将领要求主动迎击,但陆逊考虑到蜀军来势很猛,数量又不少,强攻硬打是要吃亏的。
他对诸将说:“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而且凭借高处,据守险要,很难一下子攻破,即使攻破,也难以获得全胜。
如果出击不利,影响大局,问题就严重了。
现在我们可以奖励战士,多多出谋划策,等待形势的变化。
蜀军是沿山地行军的,兵力难以施展,自然要拖得很疲乏,我们可慢慢抓住他的弱点对付他。
” 于是,陆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
他命令吴军退出山地,将几百里的让给蜀军,把部队集中在猇亭地区。
刘备对于陆逊这样的对手,没有放在心上,他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东西一线,安下了许多营寨,分散了兵力。
当刘备派兵挑战时,陆逊坚守营寨,就是不出战。
双方在猇亭对峙达六七个月之久。
蜀军被阻在猇亭夷道一线,一直找不到同吴军决战的机会,运输困难,天气渐热,斗志逐渐涣散,士气越来越低落。
这时,刘备放弃了“水陆俱进”的有利条件,将水军移到陆上,命令军队在山林中。
于是,陆逊决定反攻蜀军。
对于陆逊决定这时反攻,手下的一些将领困惑不解,说:“进攻刘备应当在他初入境的时候;现在已经让他深入五六百里,拒守已经有七八个月,一些要害的地方,他已经加固守备。
这时进攻一定是不利的。
“ 陆逊回答说:“刘备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经历多,见识广,他的军队开始集结时,各方面考虑得很细致,士气也旺盛,我们不应该同他们硬拼。
现在他们在这里驻扎了很久,没有得到进攻我们的机会,兵士已经疲劳,斗志已经消沉,策划不出什么好计谋。
所以,现在正是我们发动进攻,打败蜀军的好时机。
” 诸将认为说的很有道理,决心在反攻中取胜。
04、 为了做到有把握,陆逊先作试探性的进攻。
他先攻蜀军一个营寨,结果失败了。
但是他却从这次交锋中摸到了蜀军的弱点,想出了打败蜀军的办法。
他命令战士每人都带一把茅草,到达蜀营外,在放火的同时,猛攻蜀军,结果很成功。
接着,他率领诸军,全线出击,用同样的办法,连破四十余营,杀死蜀将 冯习、张南和 蛮族”首领沙摩柯。
蜀将杜路、刘宁等被追得无处可逃,只好投降。
在夷道包围孙桓的蜀军,也溃逃了。
刘备率领残兵败将,登上夷陵西北的马鞍山依险据守。
陆逊不给他喘息时间,集中各路兵将,四面围攻,结果蜀军溃败,被杀死一万多人。
刘备带领少数人马,乘黑夜冲出重围,逃归白帝城。
这一仗,刘备人马大部分损失掉,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丧失殆尽,元气大丧。
刘备又是羞愧、又是怨恨地说:“我竟至为陆逊所折辱,岂不是天意!” 不久,在江北的黄权,由于道路被截断,回不去蜀汉,被逼之下,率众投降了曹魏。
蜀汉有关官员请求扣押黄权妻子。
刘备说:“不是黄权辜负了我,是我辜负了黄权,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对待黄权家属,仍如同往常一样。
战争结束后,孙桓见到陆逊,称赞说:“以前我被包围时,埋怨你不派兵相救,如今,才知道你的指挥调度,实在有方啊!“孙权当然更高兴,加封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
05、 刘备逃回白帝城之后,吴军的一些将领如、潘璋等主张乘胜追击,捉拿刘备。
孙权询问陆逊的意见,陆逊考虑到曹魏虽然外示友好,内里实有奸心,很可能乘机袭击东吴后方,不宜深入蜀境,便建议孙权下了退军的命令。
刘备逃归白帝城后,改鱼腹(县治白帝)为永安,自己驻在这里,命赵云来这里守护。
刘备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成都,诸葛亮大为震动,他叹息说:“如果(字孝直)不死,一定能够劝阻主上(指刘备)东征,即或东征,也不致遭到这样的惨败。
” 这说明诸葛亮原来在伐吴的问题上,并没有持坚决反对态度。
因为荆州的丢失,影响他的整个战略部署,他是不甘心的,他不能以放弃荆州为代价,来维持吴蜀联盟关系。
他以为,刘备的东征是可以取得胜利的,没想到结果竟造成这样的局面,于是想起法正,来了一个事后叹息。
结束后不久,曹丕果然发兵进攻东吴。
原来曹丕想利用孙权有赖于曹魏的时候,加强对东吴的控制。
他要求孙权送儿子到洛阳作人质,以表示忠心,还索取大量等贡物。
孙权对曹丕物质上的要求尽量满足,索要的贡物,一一凑足奉献。
但对送子入质,孙权则以“孙登年幼,不宜入洛”为辞,婉言拒绝。
222年九月,曹丕以孙权不送质子、不听命令为由,亲率大军南征。
面对曹魏大军的进攻,孙权一方面调兵遣将,分路迎击;一方面派使臣到蜀汉求和。
兵败之余,无能为力的刘备,既担心孙权的继续进击,又担心曹魏灭掉东吴,对自己不利,便同意了孙权的和议,派使者往东吴复命。
虽然吴蜀双方讲和了,但猇亭之战的惨败,对刘备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不仅荆州没有夺回来,而且使蜀汉的元气大伤。
忧心忡忡,加上年老和过度劳累,终于使他一病躺倒了。
223年二月,刘备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派人去成都将丞相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来,安排后事。
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比曹丕高十倍,必定能够安定国家,成就大业。
假如嗣子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嗣子不行,你可以取而代之。
“ 诸葛亮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
“ 刘备又告诫刘禅和另外几个儿子说:“我死之后,你们要把丞相看作父亲一样,和他共理蜀汉。
“四月,刘备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
刘备还给刘禅留下了一个遗诏,其中有这样的话:“人活50岁就不算是短命,我已60多岁,死了没什么可遗恨的,只是非常挂念你们兄弟。
你们一定要奋勉,不可懈怠。
凡事不能以为是小恶就去做,也不要以为是小善而不去做。
你们要努力学习,可阅读《汉书》、《礼记》;闲暇时要看诸子及《六韬》、《》,可以增长人的智慧,锻炼人的 意志。
听说丞相已把《申子》、《》、《》、《六韬》等书抄写了一遍,你们可以向他请教。
” 刘备这样的托孤,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器重和信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