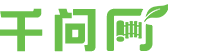欧洲中世纪的性戒律是怎样的?
【千问解读】
在欧洲的历史当中,对于“非法”性行为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
虽说在细微之处不无差异,不过在欧洲每个地区社会都会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且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
而这正式基督教文化当中的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性的起源》一书试图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
不同文化是如何对待性的,以及这些文化是如何具体表现的,这都远远超出了身体和生理行为本身——这反映的是文化关于人性、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最深刻洞见。
一、中世纪时的性况虽说每一种文明从其历史之初就规定了严厉的法则,以惩罚至少某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但是相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中世纪时对性的监管还算宽松。
传统天主教观念认为,肉体欲望应受谴责但无可避免:将其完全束缚是不可能的,并适得其反。
那时,即使是卖淫,都是受到批准的。
新教嘲笑天主教,通过允许与管理性交易,靠偷情与通奸的收益来维持自身。
“噢,罗马!”新教常常这样谴责,“妓女在做着营生,向圣洁的金库支付租金,以获取她的营业执照。
”那时的主教们可能并非出于理性考虑,但也乐得顺其自然。

非法性行为是公共罪行,这一原则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就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坚持。
现存最古老的法典(公元前2100-前1700)由巴比伦国王所制定,其中即规定通奸要被处死,大多数其他近东与古典文化同样将此视为一种严重罪行:亚述人、古埃及人、犹太人、希腊人,以及某种程度上罗马人都作如是观。
盎格鲁-撒克逊的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法典(602)就规定了各种名目的罚金:“如果一个男人与一个不属于他的寡妇结合”;与女仆或不同阶层的女奴苟合;与其他自由人的妻子通奸——在这一严重的案例中,除了高额罚金之外,罪犯须“用自己的金钱来获得一位妻子,然后将她带到别人家中”。
这些严厉的惩罚正与基督教会的态度相符,“不可奸淫”是上帝十诫的第七诫,对于每一个奸夫奸妇,他下令“必须处死”。
同样的命运也会施加于任何犯有乱伦或兽奸罪行的人身上,施加于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男子身上:所有这些人都玷污了自身与社群。
虽然《旧约》赞美婚姻是一种在社会与宗教层面都必不可少的制度,但其首要启示则是性关系乃不洁净的。
即便在丈夫与妻子之间,性仍然被严格限定于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只能为了繁衍,不可追求快乐),并且在此之后还要有洁净仪式,以洗濯这一行为带来的秽物。
早期学者们对性也不太开化,斯多噶派哲学对于性充满疑虑,将其视为一种低等与堕落的快乐。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教会的主要权威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性的消极看法。
关于节制的禁欲主义理想愈加得到强化,其主要针对神职人员,但也针对世俗男女。

要求归要求,做归做。
其实那时对性的管理还没有到十分不近情理的地步。
就连一些著名的主教,有时也是说一套做一套,至少不是那么让人信服。
圣奥古斯丁是一位十分坚定的禁欲主义者,他将色欲视为所有人类欲求中最为危险的一种。
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可是另一副样子,当他这个才子先后负笈于北非与意大利时,与一个未婚情人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并且他在当时更热衷于摩尼教而非主流的基督教。
不论在中世纪文学还是日常生活中,非法的爱情与买春之举往往以一种平常的口吻被讨论,这表明此种行为并不一定总是被谴责。
根据教会的婚姻法,在理论上讲,合法的性关系只需要双方本人的同意,无需任何牧师、见证人或仪式。
从约翰·德莱顿在1681年写的诗歌可窥见此前的性状态,《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一诗写道:在虔诚的时代,牧师开始耍起手腕/那会儿一夫多妻还不是罪恶/当时的男人到处留种/孽种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自然在怂恿,法律不阻拦/他们与妻妾纵情淫乱。
以至于公开卖淫都能得到容忍,公开卖淫在中世纪晚期逐渐得到批准。
鉴于现实中未婚的平民与神职人员不可能抑制肉欲,所以有这样的论调:与其引发诱奸、强奸、通奸以及更糟糕的行为,还不如允许妓院存在。

开始于1500年的新教运动,从内部净化教会的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一股为真理而抗争的洪流。
新教徒们怀有一种信仰,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与实践已经腐化与世俗。
他们想重新发现上帝对于基督徒的真正期待,并且据此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不仅在于宗教信仰,也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宗教改革重塑世界的活动中,性居于中心地位。
从15世纪末期开始,梅毒这一致命疾病蔓延日肆,在人群中引起了日益严重的焦虑。
由性乱引发的社会问题——犯罪、疾病、私生子、贫穷——越来越让人有切肤之感。
以更严格的标准处置通奸与偷情,实际上是晚期都铎王朝的治理举措之一。
而为了应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的反新教运动也把更为严格的性监管作为一个重要举措。
惩罚不贞之人,为了他们自身也为了社群的良善,这是一项基督教与公共的义务,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义不容辞。

新教徒认为,以往教会对于性道德的整体态度显得松弛而虚伪,软弱无力。
其神父都是好色的寄生虫:独身主义的理想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天主教的独身主义志向不切实际,对所有人而言,包括神父,婚姻是今后解决性欲的唯一合适途径。
宗教改革者们关闭妓院,逐出妓女,以及对通奸与偷情行为施以严酷的惩治。
宗教裁判所通过对身体的破坏来惩罚那些被认为是不贞的人。
他们或者被烙印上某种标记游街示众,或者直接被剥夺“作案工具”等等。
其旨在把带有污名的人从群体中区别开来,不仅是在驱逐“异教徒”,也在束缚占绝大多数的群体的自由上起到了作用。
纵观整个西方世界,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宣传与举措都强化了对于偷情、通奸、卖淫与鸡奸的压制。
新教徒的洁癖令人瞠目,甚至在女性怀孕期与经期发生的夫妻性行为,都普遍被视作违背上帝之律法——约翰·科顿在1636年为马萨诸塞与纽黑文制定的示范法典将后者认定为死罪。
1644年冬天,马萨诸塞的移民詹姆斯·布里顿公开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他提到有一次自己跟人酗酒之后,试图与一位出身很好的年轻新娘玛丽·莱瑟姆发生性关系(但未成功)。
虽然如今她已远居于普利茅斯的殖民地,但她还是被找到,最终被带到波士顿接受审判。
当时,尽管她否认双方实际发生过性行为,但她仍然被判处通奸罪。
审判过了两个星期,她被实施了绞刑,那年她只有十八岁。

新教徒们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社会,在其中,不道德行为被“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除了那些邪恶与亵渎之辈,他们被迫藏身于黑暗的角落,终日惶惶于被人揭发”。
不洁之性首先触犯了宗法原则:每一个女性都是其父亲或丈夫的财产,所以任何陌生人与之发生性关系,都得被视为一种盗窃,一种对其亲属严重的侮辱。
在当时的人们观念中,女性是比男性低级的生物,女性常常被当做物来对待。
回想一下中国古代的情形就好理解了,买卖女性、交换女性、赠送女性,这些在中国古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非法的性关系还更为实际地侵犯了财产权,比如私生子会危险别人的继承权,私生子不仅会抢去原本只属于其兄弟姊妹的财产,而且还危险乡邻。
一些地方就尽其所能地阻止穷人结婚,因为穷人养育孩子的数量超出他们自己所能承受的,会给教区增添负担。
此外卖淫不仅会传播性病,还会衍生出酗酒、行窃、欺诈、杀婴等其他罪恶。
从宗教的心理讲,人们还担心受到惩罚,不贞之举要被惩罚,要是哪个社群敢容忍这种侮辱天主之行,天主的怒火就会对他们所有人进行惩罚。

虽说对不贞之性的惩罚并不彻底,但是至少人们生活在性戒律的文化里。
在这种文化里面,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自律被视为文明的首要表征,人们之所以嘲笑不贞,不仅为了取乐,也因为那是软弱的显著标志。
传统伦理的基本准则是,男性与女性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起个人的责任,不论诱惑多么强烈。
只有兽类与野人才“没有限制地顺从”于“本性的渴求”,开化的基督徒应当让肉体处于灵魂的掌控之下。
精神和心灵对于肉体之统治乃是这一戒律文化整体之基础所在。
在性戒律施加限制的现实行为中,并不存在任何别种关于性自由之合理、适当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性监管的社会。
即使是佩皮斯的私人日记,这部在18世纪之前以最大的勇气叙述性冒险的文献之中,也充满了比后世同类著作中强烈得多的负罪感与羞耻感。
性监管并不仅仅是某种自上而下的外部强制,民众的身体力行与广泛认同使其具有了内在活力。
每个人在其中都起到了作用,甚至看守、警察与教堂执事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户主,只是在社群中各司其职罢了,并不存在单独的、专业的监管力量。
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自行监管系统,整个社群监管着自身,支持着集体行为的准则。
性戒律的文化不仅由强有力的信仰支撑,这一信仰将不道德之举视为危险。
它还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哲学与心理假设,关于政府之目的、人类之本性、信仰之伦理,以及先天理解力之缺陷。
这一戒律的施行如此长久,它与社会生活结构之缠绕如此紧密,它的思想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在1600年没有人可能设想它的废除。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