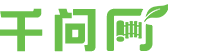刘邦是魏人,还是楚人?
【千问解读】
刘邦的先祖,史书中追溯得很远,确切可知的先人,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也称“范武子”,是“范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孙,称“刘氏”。
不过“刘氏”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人物,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移居魏国,又在秦国崛起之后,随魏惠王从旧都安邑迁居大梁。
直至战国末年,为了避秦之围,“刘氏”的一支迁徙到了丰邑,一个地处魏、楚交界的繁盛之地。
到了刘邦这一代,更是走出了丰邑,活跃在泗水之滨的沛县,这里,在秦灭六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楚地”。
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诸如“用楚爵”“好楚服”“观楚歌”“唱楚歌”之类的证据不胜枚举,但是,“丰,故梁徙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汉家天子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国籍”的呢?
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揭晓了答案: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
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婆,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
”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
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
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
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
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
”
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荆地,所以有“荆巫”,整体来看,就是刘邦祖先迁徙的时间顺序。
不过,古代注家并没有解释“梁巫”为何居于首位,毕竟,论仕宦显赫,应以“晋巫”为尊,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认同”。
 刘邦像
刘邦像
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一文中,李祖德考证指出,刘邦祖先自前430年被魏国虏获,移居大梁后,一直到刘邦祖父于前275年因躲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前后在大梁生活了155年,此时,距刘邦出生还有19年或28年。
此后,一直到前209年刘邦起兵,其家族在丰邑生活66年,正因为刘邦家族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刘邦葬在丰邑的先人,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代,故此,《汉书·高帝纪》中称“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而“坟墓”在先秦时代,有着远比居住地更重要的意义。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鲁国临难时,孔子说,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理由却是: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鲁国是我们的先人生前、死后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并不是他的,是鲁君的,他也并非为鲁君挺身而出,而是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历史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以此言之,追述先祖神灵,以先后排列顺序自无不妥,也就是“晋巫”“秦巫”“梁巫”“荆巫”。
但是,刘邦立为天子之后,他的王朝自成大宗,祖先回溯自当以他本人为起始,远祖所居国的“晋巫”“秦巫”因为年代久远,依“小宗五世而迁”的宗法制度,早已分宗多次,实则与他本人关联不大。
真正在“五世”“五服”的祖宗之列的,实则只有梁地和荆地的先祖。
在《汉书·高帝纪》的“赞”中写道:
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丰公,盖太上皇父。
也就是说,刘邦在父亲健在、生母客死他乡的情况下,与丰沛之地的“坟墓”关系,最多只有祖父“丰公”一代,以他一人来定义“父母之邦”无疑欠妥。
综上所述,自汉高祖上溯五世祖宗,坟墓多在梁地,荆地只安葬着丰公一代,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荆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而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而非“荆”。
相对于首迁的丰公而言,太公和刘邦两代都生在丰邑,对这片土地已经极有感情,见《西京杂记》卷二: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
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
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
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
高帝既作新丰,幷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
太上皇移居长安,住在深宫内,心情苦闷悲伤。
高祖私下向左右侍从询问缘故,得知太上皇平生喜好,都是屠夫商贩、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市井生活。
现今宫里啥也没有,所以快乐不起来。
于是刘邦营造新丰,迁徙家乡故人来住满这里,太上皇就高兴了。
这也是新丰这个地方多市井细民,而少有衣冠显贵子弟的缘故。
除了搬迁人口,刘邦年轻时经常祭祠枌榆之社,等到移来新丰,也原样建立。
刘邦营造新丰城邑后,一同迁移了旧社, 街巷房屋,所有景色物象全是老样子。
丰邑迁来的男女老幼,一起站在路口,各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屋子怎么走;把狗羊鸡鸭放于大道上,竟然也认得自己的家。
这种原样复制,满足了太上皇的思乡之情,也满足了他自己的,见《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
刘邦自述生长于丰邑,难以忘怀,也正因为“爱”,所以对丰邑父老跟随雍齿反叛自己依附魏国的过往切齿痛恨。
而“生长”是和土地挂钩的,所以,刘邦营造新丰,连丰邑的“枌榆社”也搬了过来,“邑”和“社”并立的前提下,才提到了“衢巷栋宇”,也就是街巷房舍的硬件,可见,“邑”和“社”是抽象家乡概念的核心载体,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
《礼记·祭法》中说: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对此,郑氏注曰:
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
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
可见,按照礼制,大夫、士、庶人都没有资格单独为自家“立社”,要与民聚族而居,且百家以上,才能共同立社,也就是东汉末年的“里社”。
这些都说明,“社”虽然供奉着土地神明,却源于各家“共立”,它因为“人”而存在,具有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而与东汉末年的“里社”并不相同,郑玄所见的“里社”经过两汉四百年的改造,已经深受政权的干预,名为“官社”,与之相对的则是“私社”。
枌榆社在先秦周礼时代,只能是“私社”,甚至不能称之为“里社”。
上引《西京杂记》内容说明,刘邦是将枌榆社与丰邑一道搬迁至关中,而枌榆社并不在丰邑中,在丰邑东北十五里,这就出现了矛盾,枌榆社到底是“邑社”,还是“里社”?
所以,《史记集解》中提出了一个解释:
或曰枌榆,乡名,高祖里社也。
翻译过来就是,枌榆社是枌榆乡的“社”,刘邦家在此乡,故而以枌榆社为“里社”。
问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写得很清楚: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
沛、丰邑、中阳里,哪怕以秦汉地方区划来看,沛为县级,丰邑为乡级,中阳里为里级,三级归属清晰明了,根本没有“枌榆乡”插入的空间,所以,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以楚国的地方管理制度来看,就根本没有“乡”这一级单位,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沛地入秦之前,刘邦曾经祭拜多年的“社”,当然不能虚构一个“乡”的概念出来。
所以,枌榆社只能是“丰邑人”共同设立的“置社”,按照陈胜、吴广所见的,也可以称为“丛祠”,就是在林木丰茂的地方举行“社祭”,参与者,自然是这一群“故梁徙也”的移民者,这非但不是“梁人”被荆楚文化征服,反而是一群“梁人”借助楚国的文化宽容,更加紧密地报团取暖。
否则,也不至于到了秦二世二年十二月在魏将周市的一纸书信下反叛,要知道,刘氏迁丰在前275年,而雍齿反叛在前209年,长达66年时间,三代人都过去了,丰邑人还自认为自己是魏国人,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抵抗同乡刘邦率领下的楚军。
其实,这种认同,在刘邦的身上一样有痕迹。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写道: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
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秦灭大梁事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张耳家在外黄,担任魏国的外黄县令,刘邦曾经在这之后,多次跟随张耳,为宾客数月之久。
这一方面因为张耳有养客之名:
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
乃宦魏为外黄令。
名由此益贤。
作为亡命逃犯,在外黄娶到了美貌多金的女子,又得到了巨额的金钱资助,所以能够“致千里客”,又当上了魏国的官吏,名声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秦灭魏之后,听说张耳是“魏之名士”的千金悬赏。
不仅如此,就连陈胜和“左右”都听说过他的名声:
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馀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胜等人之前听说过很多次张耳和陈馀的贤名,可惜没见过本人,见到了,当即大喜过望。
这些对张耳、陈馀社交影响力的记载,让刘邦青年时代的游历选择显得顺理成章。
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向南、向西,寻找楚国的名士?难道楚国就没有能“致千里客”的贤人公子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找: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
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一个“微”字,点明刘邦当时的身份,一个“少”字,说明了他当时的年龄,很年轻的时候就屡屡听说信陵君贤能,等到当了皇帝,只要经过大梁,就要祭祀信陵君,在高帝十二年,打完英布,也是刘邦人生最后一战后,他为信陵君安排了守陵户5家,要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次祭祀信陵君。
这个待遇,看起来并不起眼,却要看和谁在一起,见《汉书·高帝纪》: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
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
”
信陵君的守陵户标准与赵王一样,还是在魏安釐王已经安排了10家的同时,无疑说明,刘邦对信陵君的尊崇是非政治性的,就是“少年圆梦”,而在他年少微时,对于曾经做过信陵君宾客的张耳,当然爱屋及乌。
说到底,刘邦向着“大梁”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正是他对“魏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国别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下文中会具体展开,而具体到刘邦身上,在战国七雄制度中充斥着“畿服之制”“都鄙之制”“国野之制”,乃至于秦国的“都离之制”传统的情况下,刘氏家族曾经在大梁居住的身份,远比在楚国边鄙小邑时,距离一国权力核心更近。
具体到太公与刘邦两代的身份认同,仍是倾向于“魏人”,而非“楚人”。
另见包山楚简《集箸言》(简138反)中记录楚怀王时的法律: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
这是对证人资格的规定,与当事人同一“社”的成员、同一“里”的居民、同一“机构”的同事,以及亲属关系比堂兄弟近的,不允许作证。
从父兄弟,也就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才在亲近程度上达到“同里”“同社”“同官”的水平,这也是楚国法律上折射的家族伦理,应该是底线性的规则。
而刘邦祖父“丰公”在公元前275年定居于丰邑,“太公”崩逝于前197年,相隔78年,考虑到当时人的普遍寿命,“太公”大概率也是生于丰邑,那么,“丰公”的迁徙,恐怕不会是“独门独户”,而是与昆弟、族亲同行。
见《汉书·荆燕吴传》:
高祖从祖昆弟也。
“从祖”就是祖父的兄弟,刘泽和刘邦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他的身份,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却写作:
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
“丰公”亲兄弟的孙子,与刘邦没出“五服”就已经算是“疏属”,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楚制下,从父兄弟才算“亲属”的法律原则。
但是,更吊诡的是荆王刘贾,《汉书·荆燕吴传》中写作:
高帝从父兄也。
即刘邦的堂兄,应该算是“亲属”了吧?
在《史记·荆燕世家》中的表述,更加疏远: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
“太公”亲兄弟的儿子,刘邦的堂兄,“不知其何属”,这展示出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宗亲关系,刘邦兄弟、子侄关系的凉薄,则折射出的是这个“魏人”家族迁居楚地后,并未聚族而居,而是各过各的,这种以小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无疑更接近于秦制。
原因很简单,见桓谭《新论》:
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
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
从这个意义上看,汉王朝覆灭秦帝国之后,迅速地“汉承秦制”重建秩序,早有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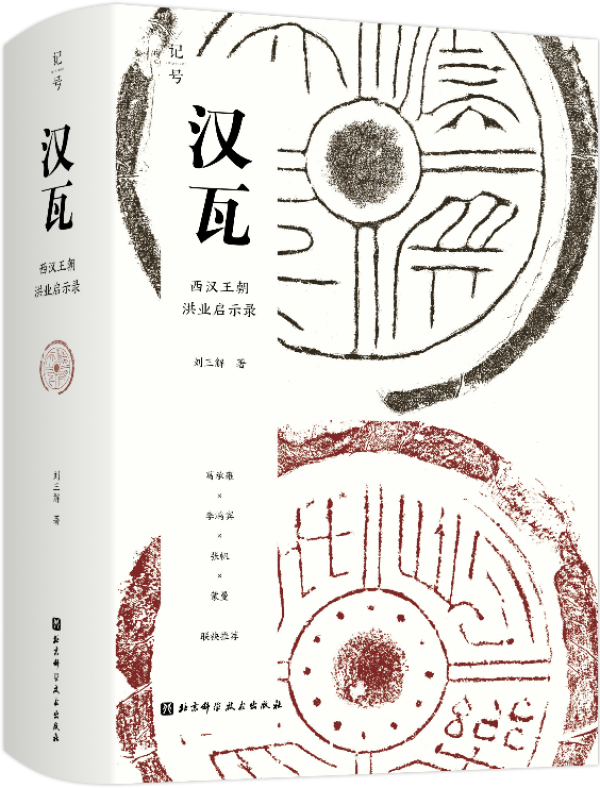
本文选自《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刘三解 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记号Mark,2021年10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进步的反义词是什么及造句
你知道有哪些广为流传的反义词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进步的反义词是什么及造句,欢迎大家分享 进步的反义词: 落后、后退、倒退、停顿、落伍 词语注音 jìn bù 英文翻译 (向前发展) advance; progress; improve; step foreward; move foreward 基本词意 (1) (动) 人或事向前发展;比原来好。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作谓语) (2) (形)适合时代要求;促进社会发展的。
进步思想。
(作定语) 为更好地掌握这个词语,以下是进步造句: 1、参天的大树是一枝一杈长起来的;学习的进步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
2、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眼睛是知悉现代进步与发展的专家。
眼睛看齐了世界的狂飙,自己也是不会落后的。
眼睛看齐了知识的飞越。
自己的头脑也不会是一片空白与虚无。
眼睛看齐了“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的哲理,自己终究会成为一位令人眼亮的举足的人物。
4、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这个时代的音乐,音乐永远都是人们追宠的对象。
我也非常的喜欢听音乐,在不同的心情里挑选着不同的音乐。
5、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6、做老师很辛苦。
但只要看到学生的进步,他们会忘掉辛苦,心里会由衷的高兴。
老师经常的鼓励同学:“努力点!坚持努力就会有收获。
”可谓是燕儿吐哺,高风亮节啊! 7、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
9、只要有梦,我就会不松懈的奋斗下去;只要有点滴进步,我就会更加的努力;只要我永不放弃,成功的希望就会一直陪伴着我。
10、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文明的象征;书,是开启智慧之门的唯一一把金钥匙;书,是横渡智慧神河的一叶扁舟;书,是攀登上科学之巅的一条山路;书,是至高无上的。
11、火对人们来说,是进步的象征。
有了火,人们不再茹毛饮血,从此懂得,火烧出来的食物更加美味,更加营养。
12、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
13、科学的伟大进步,来源于崭新与大胆的想像力。
14、胜利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提高自己。
我们只要每天进步百分之一,那就是成功。
拓展延伸 1、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 2、我的学习成绩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3、“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就是退步。
4、这学期,小林在学习上有明显的进步。
5、希望你不断努力,祝你不断进步。
6、鲁迅先生是进步青年敬仰的导师。
7、树立新风,破除陋习,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8、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9、表扬是鼓励进步的手段,不是目的。
10、开学以来,我们班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11、看到同学们的进步,老师的心里非常愉快。
12、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和爱护进步青年。
13、开学以来,小林在学习上确实有很大进步。
14、这学期,小刚学习用功,进步很快。
15、一个人有缺点就不要怕别人指出,否则,永远也不会进步。
16、只有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不断进步。
17、学习的进步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18、作为新教师,姐姐能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因而教学工作进步很快。
19、鲁迅先生是进步青年仰望的文学家。
20、对同学微小的进步,老师也给予肯定和鼓励。
2025年立德协进中学中考录取分数是几?
2025年暂未宣布,以下是今年的录取分数线。
1、2025年立德协进中学中考录取分数2025成都市立德协进中学中考收分线:统招564分,调度578分2018成都市立德协进中学中考收分线:统招543分,调度578分2017成都市立德协进中学中考收分线:统招557分,调度583分2、立德协进中学近期举动思恩明责 逐梦启征程——成都市立德协进中学2017级结业仪式七月协进,树绿禅歌,活力盎然。
2025年7月20日下战书,我校盛大举办“思恩明责,逐梦启征程”——高2017级结业仪式。
学校指导和高三年级部分西席,与方才阅历了高考的高三学子齐聚协进学术厅,配合见证高2017级学子高中生活生计的美满闭幕。
仪式上,杨书文校长揭晓热忱弥漫的结业致辞,他向一切高三教师的勤劳支出暗示感激,同时也向结业生表达了真诚的祝愿和殷切的希冀。
杨校长在致辞中夸大,寻求诗意人生,惟有存心“虚度”,所谓“虚度”是指在伟大的糊口中,修养艺术审美,据守“鉴真、从善、尚美”的信条;在理论中,融汇中西古今,广博学问、博识见地、加强胆识;在百舸争流的时期,与平易近族再起伟业同频共振,寻求“树德、犯罪、立言”的人生大志。
高三年级组长李大春,代表高三部分西席向行将结业的学子奉上结业寄语。
李教师回想了三年来与门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并鼓励门生持续承袭协进肉体,沉着淡定的驱逐人生中的每一个应战。
家长代表李师长教师代表部分家长向教师们三年来的勤劳支出暗示感激,并鼓舞高三学子们在未来的进修糊口中持续遵守协进“智、勇、纯、朴”的校训,做一位有家国情怀、道德崇高、勇于担任、砥砺斗争的追梦人。
随后,来自高三结业生张璐楠、周怅然、童小芮同窗别离用跳舞,展现了属于高三年级的芳华风度,歌曲《小荣幸》的演唱也把全部结业仪式的氛围推到了飞腾。
相关热词搜索:成都市 立德 中学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