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女诗人李因是个怎么样的人

</p><p>那今天准备和大家介绍一位距离我们更近的女诗人——李因。
</p><p>李因生于明末,曾是浙江名妓,后来嫁给了光禄卿葛征奇为妾,她的诗作也是红极一时。
</p><p>不过据说李因为人十分自负,她经常把自己比作“诗佛”王维,可见其心气
【千问解读】
说到历史知名的女诗人,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李清照、蔡文姬、唐婉等人。
那今天准备和大家介绍一位距离我们更近的女诗人——李因。
李因生于明末,曾是浙江名妓,后来嫁给了光禄卿葛征奇为妾,她的诗作也是红极一时。
不过据说李因为人十分自负,她经常把自己比作“诗佛”王维,可见其心气之高。
下面就来讲讲李因的生平事迹,如果对这位女诗人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啦。

李因,字今生,号是庵,又号龛山逸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而韶秀”,自小爱上读书习画,这是天赋使然,家中十分贫困,“积苔为纸,扫杮为书,惟萤为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家境中,诗画“便臻其妙,年及笄十三四呀,已知名于时声名远播江浙一带”,然而,刚刚及笄之年,家庭所迫,坠入风尘,成了妓女,可怜的小李因。
在当时,那些官宦士子,不思拯救将倾的大明王朝,整日花天灯地,进出灯红酒绿,握绿摧红揉蕊,留恋声色,也让明末娼妓业达到鼎盛。
李因由于才华出众,又风采非凡,得到江南名士葛征奇的垂青,纳为小妾。
葛征奇,字无奇,号介龛,浙江海宁人,明末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擅长作诗,精于绘画。
二人情同趣合,相互欣赏,伉俪情深,很幸福,遇见葛征奇是多么的幸运。
据说葛征奇纳她为妾,是看到她写的《吟梅诗》中有“一枝留待晚春开”之句,对其才华大加赞赏,想不到风尘之中,会有如此女子,顿生倾慕与怜惜之心,纳为侍妾。
从此李因随着葛征奇的工作调动,“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十五年间几乎跑遍半个中国正应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到处奔波对于李因是无价的财富呀,依旧孜孜不倦,嗜书成癖,即使在旅途,无论舟船上还是驴背上,均不忘读书吟诗。
时值明末,天下大乱,起义军烽起,到处强盗流匪,一次乘舟过宿州,突发兵变,她顾不上行李首饰贵重之物,独抱着诗稿而逃一个痴女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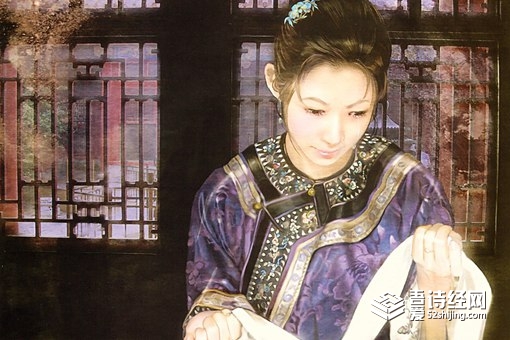
明朱由检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因集多年所写之诗,出版了诗集《竹笑轩吟草》和《续竹笑轩吟草》各一卷,共二百六十余首诗,几乎都是旅途所作,其诗风清奇,有中唐遗韵,葛征奇为她的诗集作序中称其诗“清扬婉妩,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自成逸品,即老宿臣公不能相下”看来这文学艺术,天赋十分主要呀,时下以诗人自居的人很多,那文字朽木枯藤,没有一点生机,无病乱呻吟,有辱斯文。
欣赏一下李因的《郊居用松陵集韵》:
避世墙东住,牵船岸上居。
两分三径竹,晴曝一床书。
上坂驱黄犊,临渊网白鱼。
衡门榛草遍,长者莫停车。
看似信手拈来,是那么清新又有生活,没有斧痕。
这其中提到的《松陵集》是指晚唐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互相唱和的诗集。
集中有陆龟蒙诗《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是说陆龟蒙郊居避世,皮日休字袭美题诗数首,陆龟蒙就写了这十首酬和酬谢,其中一首云:“近来唯乐静,移傍故城居。
闲打修琴料,时封谢药书。
夜停江上鸟,晴晒箧中鱼。
出亦图何事,无劳置栈车。
”
李因就是用的这首原韵,很有生活情趣,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李因的《鹫岭山庄寻秋》:
十丈陡崖挂薜萝,参云峰顶见嵯峨。
闲搜怪石秋林晚,独听残钟晓月过。
黄叶山前人迹少,白云天际鸟声多。
冷泉亭下潺潺水,不许渔舟唱棹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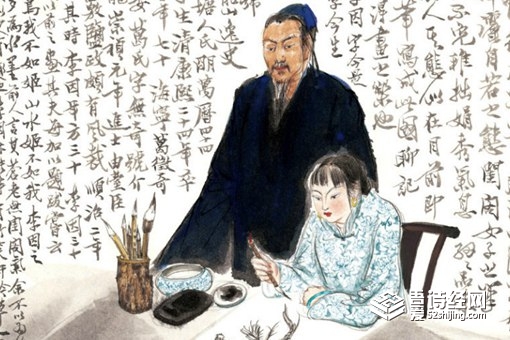
这诗大气磅礴,没有一点小女人气,笑傲多少男诗人不丈夫,这超出一般的大境界,羞杀“放歌体”,面对动荡战乱,李因慷慨激昂地写下“徒怀报国惭彤管,洒血征袍羡木兰”的诗句。
秋天将过半,诗人到处吟秋,留下一行行文字,真的该从古诗词中学习精髓,不仅仅是画葫芦,来读读李因的一首《长安秋日》,高下自悟:
高树秋声入梦迟,夜来风雨簟凉时。
季鹰自解归来好,纵乏莼鲈也动思。
李因与丈夫葛征奇有着共同的文化情趣与艺术素养,也常常以诗歌的形式交流。
李因有《舟发郭县同家禄勋赋》:
拂衣去去急,白发半愁中。
过客天涯少,行橱榾柮空。
禅关山月黑,鱼栅夜灯红。
松菊闻无恙,锄书可耐穷。
表达了他们的生活志趣。
葛征奇去世,她悲痛地写下《哭介龛禄勋公》:
秋声风急闭重关,泪寄潇湘疏竹斑。
莫问苍梧多少怨,至今石化望夫山。
诗中用娥皇、女英泪湿斑竹的典故和望夫山的意象,深切地表达出自己的悼亡之痛心。

李因不仅诗写的好,,绘画也十分了得,擅长山水写生,经名家叶大年指点,在花竹、禽鸟方面尤佳,自信自负的她,自比唐代王维。
书法与山水画以宋代大家米芾父子为宗,多用水点墨“以烟云掩映树石”,苍劲无闺阁气。
花鸟画以陈淳为师,不仅得陈淳之真髓,还注重师法造化,追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大境界,抛开了女性习画惯有的构图小气,笔致纤弱等弊病,以潇洒随意、疏爽隽逸的艺术风貌备受时人赞许。
清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中对李因的花鸟画评介颇高:“水墨花鸟苍古静逸,颇得青藤徐渭、白阳陈淳遗意,所画极有笔力,无轻弱态,当时名誉甚隆,真闺阁翘楚也。
”
自负的葛征奇感叹地说:“花鸟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
葛征奇去世时,李因刚刚三十五岁,此后她没有改嫁,又自己生活了四十年,穷困凄凉,四壁萧然,几近家中除了书画无余物,有时连烧火做饭的柴火都没有。
李因以纺织为生,兼作画自给为生,虽然经清顺治、康熙两朝,却始终以明人自居,在画中从不署清朝的年号,体现了傲骨,令人肃然起敬,晚年仍发奋学习,写作习画,在诗中写到“白发蓬松强自支,挑灯独坐苦吟诗”,后人评曰:“沈郁抗壮,一往情深,有烈丈夫所难为者”。
停下笔,从室内踱出来,秋高气爽,我仿佛看到每一朵云都流动着古代的记忆,灵魂原来是寂寞的,而寂寞的岁月并没有掩去明末女子李因那颗高贵的心灵。
风摇动着故事,那天空划过的痕迹,留下美丽的永恒。
剃发易服:孙之獬与清初统治策略的必定性探究
尽管孙之獬因首倡此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深入分析清初政治生态与民族政策,可发现剃发易服本质上是满洲统治集团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孙之獬的奏议仅是加速政策落地的催化剂。
一、清初剃发易服政策的早期实践 清军入关前已在辽东地区推行剃发易服。
1618年攻陷辽阳后,即以 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 的暴力手段强制推行。
1622年后金占领辽阳时,更明确要求 官民皆剃发降 。
这种政策在1629年攻占汉儿庄、1630年围攻遵化等战役中持续实施,表明剃发易服是后金政权长期贯彻的统治策略。
清军入关后,于1644年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当日即颁布,要求 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
虽因尚存、局势未稳而暂缓执行,但这一政策始终是满洲统治者的核心诉求。
孙之獬于1645年提出的建议,恰逢清军攻占南京、南明覆灭的特殊节点,其奏议仅是顺应了清廷既定的统治方针。
二、孙之獬奏议的历史定位 孙之獬的《剃发易服疏》具有双重历史效应。
从政策层面看,其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的表述,精准切中多尔衮巩固统治的政治需求。
该建议使清廷找到 以发式辨顺逆 的合法性依据,加速了政策落地。
从历史评价看,孙之獬的投机行为使其成为汉族阶层的众矢之的。
其剃发易服、改穿满装的举动,既未获得满洲贵族认可(满班大臣斥其 非我族类 ),又遭汉族官员唾弃(汉班大臣讽其 背祖弃宗 ),最终落得 里外不是人 的尴尬境地。
这种政治投机虽使剃发易服政策提前实施,但本质上仍属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博弈的产物。
三、剃发易服政策的深层动因 满洲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核心诉求在于摧毁汉族的民族认同。
汉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的伦理观与满洲 金钱鼠尾 辫发习俗形成根本冲突。
多尔衮深知,若允许汉族保留传统衣冠发式,将导致 汉化则亡国 的政治风险。
因此,剃发易服既是文化征服手段,更是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环节。
经济与军事层面的考量同样关键。
剃发易服政策可降低统治成本:通过统一服饰发型,便于区分顺民与反抗者;通过摧毁汉族传统纺织业,削弱地方经济基础;通过强制推行满语满文,瓦解汉族士大夫的文化特权。
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改造,为清廷建立 首崇满洲 的统治秩序奠定基础。
四、孙之獬个人命运的历史隐喻 孙之獬的结局印证了剃发易服政策的反噬效应。
1647年山东起义中,起义军以 种发 之刑(用锥子刺孔插猪毛)羞辱这位 剃发令始作俑者 ,最终将其凌迟处死并灭其三族。
清廷对此未作任何抚恤,反而默认民间对其 汉奸 的定性。
这种 主子不认、百姓痛恨 的处境,暴露出政治投机者的必然悲剧。
更深层的示在于,孙之獬的命运折射出清初统治策略的内在矛盾:当暴力手段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任何工具性人物都可能沦为弃子。
剃发易服政策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清廷统治,但埋下了 反清复明 思想长期存在的隐患,最终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孙之獬与剃发易服政策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碰撞的缩影。
即便没有孙之獬的奏议,清廷仍会基于统治需求推行该政策,只是时间早晚与实施力度的问题。
剃发易服作为清初民族政策的典型样本,既展现了满洲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也暴露出文化征服的局限性。
这场持续三十七年的文化改造运动,最终在的 剪辫令 中画上句号,印证了强制同化难以消除文化基因的历史规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剃发易服:孙之獬与清初统治策略的必定性探究
尽管孙之獬因首倡此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深入分析清初政治生态与民族政策,可发现剃发易服本质上是满洲统治集团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孙之獬的奏议仅是加速政策落地的催化剂。
一、清初剃发易服政策的早期实践 清军入关前已在辽东地区推行剃发易服。
1618年攻陷辽阳后,即以 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 的暴力手段强制推行。
1622年后金占领辽阳时,更明确要求 官民皆剃发降 。
这种政策在1629年攻占汉儿庄、1630年围攻遵化等战役中持续实施,表明剃发易服是后金政权长期贯彻的统治策略。
清军入关后,于1644年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当日即颁布,要求 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
虽因尚存、局势未稳而暂缓执行,但这一政策始终是满洲统治者的核心诉求。
孙之獬于1645年提出的建议,恰逢清军攻占南京、南明覆灭的特殊节点,其奏议仅是顺应了清廷既定的统治方针。
二、孙之獬奏议的历史定位 孙之獬的《剃发易服疏》具有双重历史效应。
从政策层面看,其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的表述,精准切中多尔衮巩固统治的政治需求。
该建议使清廷找到 以发式辨顺逆 的合法性依据,加速了政策落地。
从历史评价看,孙之獬的投机行为使其成为汉族阶层的众矢之的。
其剃发易服、改穿满装的举动,既未获得满洲贵族认可(满班大臣斥其 非我族类 ),又遭汉族官员唾弃(汉班大臣讽其 背祖弃宗 ),最终落得 里外不是人 的尴尬境地。
这种政治投机虽使剃发易服政策提前实施,但本质上仍属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博弈的产物。
三、剃发易服政策的深层动因 满洲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核心诉求在于摧毁汉族的民族认同。
汉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的伦理观与满洲 金钱鼠尾 辫发习俗形成根本冲突。
多尔衮深知,若允许汉族保留传统衣冠发式,将导致 汉化则亡国 的政治风险。
因此,剃发易服既是文化征服手段,更是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环节。
经济与军事层面的考量同样关键。
剃发易服政策可降低统治成本:通过统一服饰发型,便于区分顺民与反抗者;通过摧毁汉族传统纺织业,削弱地方经济基础;通过强制推行满语满文,瓦解汉族士大夫的文化特权。
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改造,为清廷建立 首崇满洲 的统治秩序奠定基础。
四、孙之獬个人命运的历史隐喻 孙之獬的结局印证了剃发易服政策的反噬效应。
1647年山东起义中,起义军以 种发 之刑(用锥子刺孔插猪毛)羞辱这位 剃发令始作俑者 ,最终将其凌迟处死并灭其三族。
清廷对此未作任何抚恤,反而默认民间对其 汉奸 的定性。
这种 主子不认、百姓痛恨 的处境,暴露出政治投机者的必然悲剧。
更深层的示在于,孙之獬的命运折射出清初统治策略的内在矛盾:当暴力手段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任何工具性人物都可能沦为弃子。
剃发易服政策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清廷统治,但埋下了 反清复明 思想长期存在的隐患,最终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孙之獬与剃发易服政策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碰撞的缩影。
即便没有孙之獬的奏议,清廷仍会基于统治需求推行该政策,只是时间早晚与实施力度的问题。
剃发易服作为清初民族政策的典型样本,既展现了满洲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也暴露出文化征服的局限性。
这场持续三十七年的文化改造运动,最终在的 剪辫令 中画上句号,印证了强制同化难以消除文化基因的历史规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