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巴黎,激情奥运,本届奥运会四个最令人瞩目的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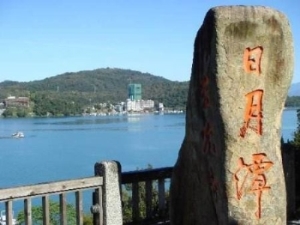
现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两天,让我们一起看看本届奥运会都有哪几个最吸引人的看点。
金牌榜第一之争,谁将成为新的体坛盟主 金牌榜第一之争,永远是奥运会上最热的看点。
从近几届奥运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本届奥运会的金牌榜第一之争,又将再一次在中美
【千问解读】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来了,这次,充满激情的奥运会再一次来到了世界浪漫之都巴黎,让世人格外充满了期待。
现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两天,让我们一起看看本届奥运会都有哪几个最吸引人的看点。
金牌榜第一之争,永远是奥运会上最热的看点。
从近几届奥运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本届奥运会的金牌榜第一之争,又将再一次在中美之间展开。
这次在巴黎,美国队的气势依然是咄咄逼人,他们派出了592人的最大运动员队伍,目标当然是剑指金牌榜第一的。
中国队虽然在运动员总数上明显不及美国,只有区区的405人,但中国队历来成功率比较高,特别是金牌数占奖牌的比例多数情况下均高于美国队。
在俄罗斯人大部分缺席的巴黎奥运赛场上,中美第一之争将会白热化到什么样的程度,让我们所有人拭目以待,看中美激烈比拼后,谁会登上体坛盟主的宝座。
近年来,以四年一届奥运会为代表的体坛,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中美稳居第一梯队,霸占金牌榜前两位,第二梯队国家五、六个,他们竞争金牌榜第三名。
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上,从运动员队伍的规模、整体实力及其他场外因素分析看,有实力竞争金牌榜第三名的队伍,按可能性顺序依次为: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
通观历届奥运会,首金总是许多有实力的队伍必争项目。
本届奥运会,首金将再次在射击场诞生。
射击,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就是射击项目贡献的,也多次在奥运会上,由射击夺得首金。
巴黎奥运赛场,中国队再次迎来了夺取奥运首金的机遇。
射击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项目是中国的强项,中国队派出了盛李豪、杜林澍、黄雨婷、韩佳予四员小将出战。
他们是清一色的00后,届时能否顶住压力,打出应有的水平,射落这枚万众期待的金牌,我们拭目以待。
历届奥运会上,游泳都是一个较早开赛的大项目。
本届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更将吸引许多观众的目光,从目前的报名参赛队伍来看,美国46人,澳大利亚41人,中国31人。
这三支队伍目前基本代表了当今世界泳坛的最高地位。
虽然美国一直垄断着世界泳坛,但这次在巴黎,澳大利亚和中国能否在泳池里激起更高的浪花,憾动美国的统治地位,值得我们期待。
毛姆:生于巴黎的英国文学巨匠
这位以《月亮与六便士》《人性的枷锁》等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虽在法国巴黎诞生,却以英国公民身份终其一生,其创作轨迹与身份认同始终交织着英法两国的文化印记。
一、双重文化基因:从巴黎到伦敦的成长轨迹 毛姆的出生地巴黎,赋予他法国文化的蒙。
其父罗伯特·奥蒙德·毛姆是英国驻法大使馆的律师,母亲爱达·艾格尼斯则出身英国中产家庭。
然而,命运的转折在毛姆8岁时降临:父母双亡后,他由担任牧师的伯父抚养,被迫离开法国,回到英国肯特郡的惠特斯特布尔。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其创作,如《人性的枷锁》中主角菲利普·凯里自幼寄人篱下的孤独,便源自毛姆的童年记忆。
在伦敦学医期间(1892-1897年),毛姆接触到底层社会,这段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素材库。
他笔下的伦敦贫民窟、医院病房与景象,均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尽管持有英国国籍,但法国文化始终是其精神底色——他精通法语,酷爱法国文学,晚年定居法国里维埃拉,甚至在遗嘱中要求将部分骨灰撒入地中海。
二、文学身份的构建:从“二流作家”到“故事圣手” 毛姆自嘲为“二流作家”,却以独特的叙事风格重塑了英国文学格局。
他打破道德说教传统,开创“旁观者叙事”风格,以冷静笔触剖析中产阶级虚伪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以法国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探讨艺术与世俗的冲突,其全球销量超千万册,被译成50余种语言。
在英国文坛,毛姆的“异质性”尤为突出。
他既批判(如短篇小说集《一片树叶的颤动》),又揭露英国社会的伪善(如《刀锋》对战后虚无主义的反思)。
这种跨文化视角,使其作品既保持英国文学的严谨逻辑,又融入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形成独特的“毛姆式”叙事。
三、国籍认同的复杂性:从文化归属到社会角色 尽管毛姆在护照上始终是英国公民,但其法国血统与长期旅居经历,使其身份认同充满矛盾。
他拒绝加入英国国籍协会,曾公开表示:“我首先是巴黎人,其次才是英国人。
”然而,在政治立场上,毛姆始终忠于英国:一战期间,他加入英国情报部,以间谍身份活跃于瑞士与俄罗斯;二战时,他赴英美宣传抗德,被授予“荣誉侍从”称号。
这种矛盾在《面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人公凯蒂在婚姻幻灭后,于中国霍乱疫区完成自我救赎,其经历恰似毛姆本人在东西方文化间的徘徊。
正如他所说:“人最大的悲剧不是孤独,而是用喧嚣逃避孤独。
”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深刻反思,使其作品超越了国籍的局限。
四、历史定位:跨界的文学遗产 毛姆的国籍之争,本质是文化归属与文学成就的辩证关系。
他虽生于法国,但以英语写作,其作品被纳入英国文学经典;他虽批判英国社会,却始终以英国公民身份参与历程。
这种复杂性,反而成就了其作品的普世价值——无论是《寻欢作乐》对人性弱点的洞察,还是《卡塔琳娜》对西班牙历史的重构,均展现出超越地域与时代的艺术魅力。
1965年,毛姆在法国病逝,其墓碑上镌刻着《人性的枷锁》中的名句:“我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智慧,我的灵魂因此而获得了平静。
”这句墓志铭,恰似对其一生的总结:一个生于巴黎的英国人,以文学为桥梁,连接起英法两国的文化血脉,最终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毛姆的国籍之谜,恰是其文学价值的隐喻。
在全球化时代,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归属,不在于出生地,而在于对人性永恒命题的探索。
正如他在《刀锋》中所写:“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智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这位“故事圣手”用一生证明,文学的疆域,永远超越国界的边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毛姆:生于巴黎的英国文学巨匠
这位以《月亮与六便士》《人性的枷锁》等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虽在法国巴黎诞生,却以英国公民身份终其一生,其创作轨迹与身份认同始终交织着英法两国的文化印记。
一、双重文化基因:从巴黎到伦敦的成长轨迹 毛姆的出生地巴黎,赋予他法国文化的蒙。
其父罗伯特·奥蒙德·毛姆是英国驻法大使馆的律师,母亲爱达·艾格尼斯则出身英国中产家庭。
然而,命运的转折在毛姆8岁时降临:父母双亡后,他由担任牧师的伯父抚养,被迫离开法国,回到英国肯特郡的惠特斯特布尔。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其创作,如《人性的枷锁》中主角菲利普·凯里自幼寄人篱下的孤独,便源自毛姆的童年记忆。
在伦敦学医期间(1892-1897年),毛姆接触到底层社会,这段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素材库。
他笔下的伦敦贫民窟、医院病房与景象,均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尽管持有英国国籍,但法国文化始终是其精神底色——他精通法语,酷爱法国文学,晚年定居法国里维埃拉,甚至在遗嘱中要求将部分骨灰撒入地中海。
二、文学身份的构建:从“二流作家”到“故事圣手” 毛姆自嘲为“二流作家”,却以独特的叙事风格重塑了英国文学格局。
他打破道德说教传统,开创“旁观者叙事”风格,以冷静笔触剖析中产阶级虚伪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以法国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探讨艺术与世俗的冲突,其全球销量超千万册,被译成50余种语言。
在英国文坛,毛姆的“异质性”尤为突出。
他既批判(如短篇小说集《一片树叶的颤动》),又揭露英国社会的伪善(如《刀锋》对战后虚无主义的反思)。
这种跨文化视角,使其作品既保持英国文学的严谨逻辑,又融入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形成独特的“毛姆式”叙事。
三、国籍认同的复杂性:从文化归属到社会角色 尽管毛姆在护照上始终是英国公民,但其法国血统与长期旅居经历,使其身份认同充满矛盾。
他拒绝加入英国国籍协会,曾公开表示:“我首先是巴黎人,其次才是英国人。
”然而,在政治立场上,毛姆始终忠于英国:一战期间,他加入英国情报部,以间谍身份活跃于瑞士与俄罗斯;二战时,他赴英美宣传抗德,被授予“荣誉侍从”称号。
这种矛盾在《面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人公凯蒂在婚姻幻灭后,于中国霍乱疫区完成自我救赎,其经历恰似毛姆本人在东西方文化间的徘徊。
正如他所说:“人最大的悲剧不是孤独,而是用喧嚣逃避孤独。
”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深刻反思,使其作品超越了国籍的局限。
四、历史定位:跨界的文学遗产 毛姆的国籍之争,本质是文化归属与文学成就的辩证关系。
他虽生于法国,但以英语写作,其作品被纳入英国文学经典;他虽批判英国社会,却始终以英国公民身份参与历程。
这种复杂性,反而成就了其作品的普世价值——无论是《寻欢作乐》对人性弱点的洞察,还是《卡塔琳娜》对西班牙历史的重构,均展现出超越地域与时代的艺术魅力。
1965年,毛姆在法国病逝,其墓碑上镌刻着《人性的枷锁》中的名句:“我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智慧,我的灵魂因此而获得了平静。
”这句墓志铭,恰似对其一生的总结:一个生于巴黎的英国人,以文学为桥梁,连接起英法两国的文化血脉,最终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毛姆的国籍之谜,恰是其文学价值的隐喻。
在全球化时代,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归属,不在于出生地,而在于对人性永恒命题的探索。
正如他在《刀锋》中所写:“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智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这位“故事圣手”用一生证明,文学的疆域,永远超越国界的边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