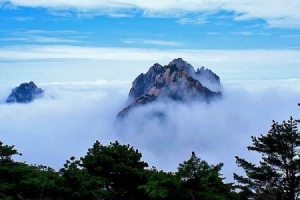关羽失荆州走麦城,真的是因为大意吗?

话说,三国时期诸多英雄豪杰,历朝历代都被世人所,尤其是,更是被后人所追捧敬仰。
就非常欣赏关羽,但
【千问解读】
话说,三国时期诸多英雄豪杰,历朝历代都被世人所,尤其是,更是被后人所追捧敬仰。

就非常欣赏关羽,但是,即使费尽心思,想尽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将关羽这个良将收于自己的麾下。
关羽败走麦城,命丧东吴之手后,曹操收到了东吴特意送过来的“礼物”(关羽的头颅),当曹操看到故人的头颅后。
随后,曹操命令将关羽厚葬,同时,让朝廷文武官员全都身着丧服为关羽举行葬礼。
在关羽被安葬后,曹操特地来到了关羽的墓前,停留许久,在这个期间,他对着墓碑言语良久,流出了不少的眼泪。
其中,曹操的一句说,揭示出关羽的真正死因。
众所周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后,刘备为大哥,关羽张飞为二弟三弟。
刘关张三人自结拜后,彼此便认定了兄弟之情,誓死不离不弃。
尤其是在小说《》中,关羽千里奔袭寻旧主的时候,更是一路保护了刘备的两个夫人。
即使曹操给关羽赐金封侯,送赤兔宝马,关羽依然没有忘记的誓言与刘备的兄弟之情。
关羽也是聪明人,怎能不知曹操对待自己的好?在关羽为曹操斩诛,解白马之围后,就认为自己算是报答了曹操的知遇之恩。
在曹操刚遇见关羽后,仅仅只是对关羽的战斗力非常欣赏,但随着长时间的相处与相知后,对关羽这个人的品行也有所了解,更开始钦佩关羽的忠与义。

因此,在关羽离开曹营时,曹操还亲自相送,并亲自为其系上了一件披风。
虽然曹操知道“放掉”关羽就是,为自己的霸业留下了后患,但曹操就是欣赏关羽,真是舍不得杀他(曹操对关羽可是真感情)。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在关羽与刘备再次重逢后,就一直追随刘备“匡扶汉室”,刘备之所以能够建立蜀汉政权,一是要感谢,二是要感谢关羽的一直追随,倘若早期没有关羽为其冲锋陷阵,那么刘备绝对不能取得如此成就。
可惜,在蜀汉最强悍的时期,关羽不幸战死。
在曹操为关羽追悼时,看着往日为自己征战解围的猛将惨死的头颅后,已然上了年纪的曹操感慨颇多。
曹操对着关羽的墓碑叨念了许久,其中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云长啊!如果你当初跟了我,你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惨死,你缺的仅仅只是一个良主”。
细想曹操的这句话,确实很有深意,此话虽然没有点破,但是也从侧面说出了关羽真正的死因。
此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关羽之死,与刘备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刘备害死关羽的。
虽然这个并不是刘备直接造成的,但是,刘备在这件事上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刘备向川蜀地区进攻时,令关羽驻守在荆州,在刘备拿下了益州后,其势力越来越大,因此刘备必须向各个要隘派遣将去镇守。
在当时,荆州周边的刘备集团势力成员有孟达、、等,这三个人与关羽的距离都很近,但有一点不好的是,这三个人与关羽的关系非常差。
荆州的战略意义之大,刘备怎能不知,但其还故意将自己的亲属安排在这里,糜芳是刘备的大舅哥,而刘封是其义子,在用人的方面,刘备仅仅只是考虑了“亲疏关系”,而并没有切实考虑实际的“人际关系”(刘备在识人认人方面确实厉害,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为何会如此“糊涂”?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此外,刘备自起家时就与关羽寸步不离,就连睡觉刘关张三兄弟都在一张床上,怎能不晓得关羽的性格,关羽的高傲是出了名的,能让关羽瞧上的,还真没有几个人。
虽然刘备深知自己二弟有性格缺陷,但他却从未对关羽提及过,关羽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唯独最信任的人就是刘备,如果刘备能够多向关羽劝言,那么,关羽的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刘备的三地张飞,喜欢酗酒与打骂士卒,刘备就曾多次对其劝说,但张飞就是改不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飞醉酒丢徐州,然后刘备对其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之,尚可缝补;手足若断,安能续否?”被后世奉为经典。
刘备这样经常劝说张飞改“脾气”,为何就不对关羽说改“脾气”呢? 虽然说曹操与刘备都是那个时期的枭雄,但在识人用人方面以及如何管教与对待属下方面,曹操比刘备更胜一筹。
大家这样来看,曹操麾下有那么多能人,有自己的嫡系,也有归降的势力,为何发生内讧事件那么少呢(主要指能臣强将)? 而在刘备麾下,明将屈指可数,在关羽最困难的时刻,没有任何援军,原本应该来的“援军”则成为了“叛军”投降了东吴。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曹操的势力中,那么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最后,话再说回来,如果关羽当初真的追随了曹操,在关羽的身上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更不会出现因自己人而惨死的情况。
曹操的那句话点明了关羽的死因,一是刘备用人不善,二是对手下管教无方(不过,刘备在识人方面确实比较厉害,用人方面就比曹操差得很远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